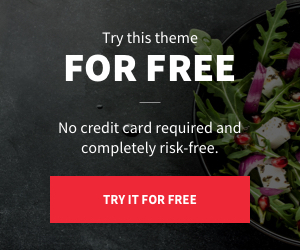伦理型文化
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,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。
上古中国是在氏族没有完全解体、血缘关系没有彻底打破的情况下进入文明、建立国家的。氏族中的男性家长,变成掌握权力的“王”。家庭(家族)中的差序关系、尊卑等级,与统治被统治的权力关系相一致。西周社会就是以血缘为自然基础、以周天子为核心、以伦理为纽带的政治—伦理结构。基于宗法结构和宗法观念,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决定地位。西周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发端期,是中国传统文化“伦理型”精神气质的塑型期。自此,中国文化以道德来破解朝代更迭的密码,以道德来阐释政权来源合法性,形成了政治—伦理一体化的传统;重视修身与教化,形成了德治主义的传统;注重道德调节、“贱讼”并推崇“无讼”,形成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传统。
虽然,自春秋以降,西周的宗法制度渐趋式微,但宗族、家族作为宗法制度的遗存,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。中国的朝代更迭史,就是一个个家族兴衰史。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门阀士族、豪门大姓,备受古人赞誉的“十世义居”、“五世同堂”,遍布各地的宗祠、族祠、祖庙,这些都说明宗族、家族以及宗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时至今日,历史上的宗法制早已不复存在,传统的宗族、家族结构受到工业社会大潮的冲击,也在悄然发生改变,但中国文化的基因已经镌刻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、行为方式中。尊宗敬祖的追远传统,孝亲敬长的人伦传统,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人文传统,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规范和理念,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,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。
整体主义型文化
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型文化,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整体主义型文化。传统文化中的“群己”之辨、“公私”之辨,个人与社稷、个人与天下的关系,都与此相关。
农业生产对水和水利的依赖极大,由此生发出个人对整体的认同意识。先秦古籍中几乎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。在治理洪水的实践中,古人发明了水利灌溉的技术。水利工程很难由个人或者单个家庭独立完成,必须依靠整体的力量集结和统筹。耕地灌溉和排水需要彼此合作、配合而不是相互掣肘。对于个人或者单个家庭来说,统合于整体之中,未必是出于自愿的联合,但出于耕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如此。因此,在农耕文明中,集体行使某种公共职能,更加需要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整体内部的协调性,个人与整体的不可分离性就显得愈发重要。
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,安土重迁的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更加紧密,强化了个人对整体的道德义务。费孝通先生曾以“乡土中国”来定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。从人与土地的关系来看,乡土社会流动性差,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老死于斯是乡土社会的常态。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,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,调控的手段是公序良俗而非法律,调控的目的是增强整体的凝聚力而非使之分崩离析。孟子在其仁政构想中,主张实行乡田同井、八家共养公田的集体耕作方式,这种方式不仅是有效率的,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关联,培养人们整体主义的道德观念。
重视整体利益,维护整体的和谐统一,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,崇公尚忠,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价值取向,而分裂整体、背叛整体、侵犯整体利益的行径,一直受到人们的唾弃。先秦各家虽思想迥异,但总体上整体主义是主流观点。必须指出的是,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背景下,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所强调的社稷、国家、天下,究其根本,不过是以整体名义出现的一家一姓的私利,不过是“虚幻的整体”和“虚幻的整体利益”。但是,从整体主义中生长出捍卫祖国统一、维护民族团结、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,“苟利社稷,生死以之”、“公家之利,知无不为,忠也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等道德理念,已经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狭小私利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,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非宗教型文化
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。从《左传》的“三不朽”到《论语》的“仁以为己任”,从《孟子》的“穷则独善其身、达则兼善天下”到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,从《大学》的“修齐治平”到明清之际的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一直遵循着用世、入世的传统,其实践品格十分鲜明。墨家倡导兴天下之利、除天下之害,摩顶放踵四处奔走,积极济世救民。有人说入则孔孟出则老庄,似乎道家是出世的,实际上道家并不是出世,它是告诉人们如何在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活中全身远祸。道家以避世的生存智慧去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,以精神的绝对自由去抵抗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,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政治智慧为治国理政提供一种模式,这是具有道家人文关怀精神的“入世”哲学。正如司马谈所言,诸子虽“言之异路”,但都是“务为治者也”。他们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,关注现实问题,回应时代困惑,用理论去干预现实,奠定了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。
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。中国文化虽讲鬼神,但总体上对鬼神持理性的态度。殷人的天帝崇拜在周初被重新改造,周公将殷人尊奉的至高无上人格的“天帝”创造性地诠释、改造为可以与人沟通的主宰,并引入“德”,试图从人自身而非人之外去寻找权力转移的因素。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虽未否定神、天的存在,但他们更强调人、人事、人道的重要性,把吉凶、祸福、治乱的根源归结为人自身。汉代以后,桓谭、王充对迷信的批判,两晋南北朝时期戴奎、何承天、范缜对于佛教的批判,都是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传统文化不否认鬼神的存在,他们认为鬼是去世的祖先和亲人,是祭祀的对象,要理性对待,敬之远之。受中国文化是非宗教型文化的影响,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教合一、宗教高于政权的情况;没有出现一教独大的情形,而是一方面互相争论,一方面相互汲取;从民族性格来看,中国人关注世俗生活、少讲末日来世,崇尚中庸平和、较少狂热极端。
天人合一型文化
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,但作为一个命题,则是宋代理学家张载首先提出。所谓天人合一,说的是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,认为二者相通而不相隔,相合而不相分,相谐而不相胜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,通过论证天与人相通而无二,进而回答人的道德是从哪来的,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问题。孟子说,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,但就因为这微小但根本性的差异,使人与禽兽截然分野。人禽之别,非别在生物特性,而是别在道德性。孟子说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;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”他认为,性不外心,性天合一,因此人要存心养性以事天。人之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存在,道德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,究其根本,源于宇宙之性与人之性相通,人秉受天之德性作为其规定性。思孟学派关于天人相通的观点,在宋明理学得到阐扬。张载明确提出“天人合一”,二程、朱熹继之,认为宇宙乃人之道德依据,宇宙之性也是人之本性,天道人道只是一道。从天的角度去论述人的道德,是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共识性观点,“宇宙本根乃道德之最高准则;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发现。……此种天人合一的观念,是汉宋儒家哲学中之一个根本观点”。(张岱年:《中国哲学大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177页)
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,强调人与宇宙自然和谐统一,反对违背自然规律、主观任性干预自然的行为。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”(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)。天地的德性是生养万物,人要尊重自然规律,方能德合天地。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倡导“爱物”,孔子“钓而不纲,弋不射宿”,孟子主张“使民以时”、“不违农时”、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,荀子在其圣王之制的构想中,提出对于山林、鸟兽、鱼类要可持续的利用,“不夭其生,不绝其长”。道家反对人为造作,老子提倡“道法自然”,庄子主张“无以人灭天”,批评违反自然导致“浑沌之死”的行为。所有这些,都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自然,反对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和竭泽而渔式地破坏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,是指主体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,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。儒家提倡修身为本,认为通过修身,人的境界可逐级攀升,最高的境界,“可以赞天地之化育”,“可以与天地参”。庄子认为 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。显然,庄子所言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,不是现实层面的合一,而是主观世界中的合一,在绝对的精神自由中,消泯是非、善恶、美丑、生死的界限,臻于齐万物、合天人的精神境界。冯友兰把人的境界由低到高逐级分为四种,即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臻于天地境界的人,已摒弃自然境界,超越功利的、道德的境界,关注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,关注自己行为之于宇宙的意义。儒家的“与天地参”,庄子所言万物一体,冯友兰的“天地境界”,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境界。
多元融合型文化
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融合型文化,这是由其内在的“和而不同”精神所决定的。西周时期思想家即提出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的深刻思想,孔子主张“和而不同”,反对“同而不和”,《中庸》提倡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”。中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包容精神,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,海纳百川以成其大,中国文化因此延续至今、薪火相传。
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,二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。
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。西方文化注重民族区分,而中国文化注重民族融合。中华民族自源头始,就呈现出多途起源、多元一体民族格局。经过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,中华民族逐渐融汇繁衍成世界第一大民族,并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。在此过程中,各个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创造主体。文化的主体是民族,民族创生文化,文化亦陶冶民族。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。《中庸》说,“今天下车同轨,书同文,行同伦”,“同伦”即指认同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。可见,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、国家认同、天下一统的重要内容,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纽带。
中国传统文化是各种不同类型、样态文化的融合。首先,从文化起源而论,中华文化自源头起,即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样态,其创生地不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,而是多元一体,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“满天星斗”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、大汶口文化,内蒙古的红山文化,甘肃的大地湾文化,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,浙江的河姆渡文化,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初创期的灿烂星河。其次,从各民族文化而论,汉代的匈奴、两晋南北朝的五胡、两宋时期的契丹和女真、唐代渤海国的靺鞨,元代的蒙古,建立清的满族,这些民族都曾经创造出自己的文化,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。他们的政权消亡了,它们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,融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没有各个民族的文化,便无以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。再次,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而论,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,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教的中国化。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,这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第一次接触。其间有激烈的冲突,更多的是碰撞、吸纳、消化与融汇。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方术,两晋时期佛教高僧进入名士圈子,将佛学义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,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广为传播,唐代佛教大盛。尽管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,甚至某些朝代一度形成自王室到民间的崇佛热潮,但并未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、儒道互补的构架,也未从根本上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、价值理想和道德观念。佛教中国化的结果,已经不同于印度佛教,被宋明理学吸收,佛教融入中国文化,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
来源: qstheory